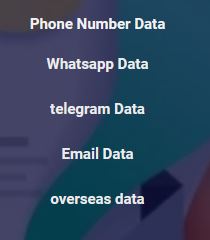因此,“阿拉伯之春”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寻找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以及危机时期欧洲和地中海地区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的可能答案。
首先,如果我们“反,我们会深深地质疑叛乱分子的自发性和勇气,但最重要的是,在缺乏政党/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能力将异议、对抗和抗议引导到具体的政治目标上(至少在部分和最后阶段,突尼斯的 UGTT 工会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发挥了作用)。多年来,欧洲也经历了一场强大的异议运动和激进对抗运动的出现,然而,这场运动无法将其力量完全引导到具体的政治目标上,因此,在面对体制和政治体系对当代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替代性叙述的强烈抵制(这往往演变为暴力镇压事件)时,它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但边缘的参与者。因此,“阿拉伯之春”给比较研究者提出了首要任务,即理解这场“运动”,最重要的是深入质疑其在危机时期的政治作用。
其次,如果我们继续分析导致马格里布爆发起义的至少部分原因,我们会发现自己 新西兰电报号码数据 再次面对一面“镜子”,它与席卷整个欧洲的抗议、强烈不满、愤怒、对包容和社会正义的渴望有着深刻而重要的联系。当然,我们无法消除结构性差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最重要的,初始政治体系的不同暴力和压迫性;然而,类比比人们想象的更有力,特别是如果我们从危机的(共同)视角来看待这一现象。
事实上,马格里布起义从政治角度上来说是一种绝望,其根源至少在于三个方面。
首先,青少年状况不稳定。马格里布的年轻人被高教育标准所束缚,却无法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他们向这种不确定性发起挑战,而这种不确定性往往又落入了听天由命和宿命论的泥沼,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不稳定”一词的词源。不稳定当然是指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但它也是一种“请求、祈祷、向往”,即一种构建个人经历意义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格里布的年轻反叛者能够将不稳定状态的不适(和勇气)转化为对社会和政治融合的真正要求。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